
《哲学研究》

引言
对柏拉图来说,这是通过灵魂对神圣且可理解的天界进行再回忆而发生的,灵魂曾一度在这个天界驻留。基督教里当然没有对灵魂重生的规定,更是根本没有灵魂转世一说。尽管如此,神性天界与人类精神之间一定存在着一种联系。
奥古斯丁首先勾画出一幅人类记忆的复杂图景。在记忆的帮助下,我们不仅回忆起印象、经历和概念,而且我们的记忆非常具有创造性。它对这个世界进行整理,为其塑形,还对其进行解读。记忆看起来似乎是灵魂之胃,在这里所有东西都被推翻然后再加工。它最令人惊叹的成就是我们借助记忆自我当下化的方式和方法。我们究竟从哪里知道我们是谁?如果我们根本上不是感性地感知到自己,我们的记忆又如何产生关于我们自己的印象?
没有什么比自我意识更为直接的了。奥古斯丁经过一再反复的思考证明了自我意识,这属于哲学史上最著名的思考,因为它预示了一个更为著名的思考。根据奥古斯丁的观点,我不可能严肃地怀疑我自己的意识。我存在这件事,我也不会搞错:“因为,我错故我在。也就是说,不存在的人是不会弄错的。因此当我产生错觉时,我恰好就是存在的。按照这个说法,我错故我在,如果‘我错故我在'是确定无疑的,那么我怎么会在我存在这件事上搞错呢?

因为我可能是那个被搞错的对象,所以即便我搞错了,毫无疑问我也不会把自己存在这事搞错。”直到千余年过去,这番细致的思考才会迎来一阵研究热潮,并成为哲学的全新开端。我们说的是笛卡尔和他著名的Cogito ergo sum——“我思故我在”——三十年战争前夜,这位法国人在一间农舍里经过无前提的思考,似乎从虚无中得出了这一句话。由此,笛卡尔为哲学奠定了一个新基础——主体性的基础,并开创了一个新时代。相反,奥古斯丁决不涉及主体性思考的自我赋权。
他只想表明,就像新柏拉图主义中已有的观点一样,人可以通过深入自省来接近真理。而这个隐藏在我们灵魂深处的真理则是——上帝!好消息是,人的本性中,也确实想要去认识上帝。我们感受到一种渴望,要去认识我们自己,并达至我们真正的本质。值得关注的是,奥古斯丁将这一渴望称为爱。在所有“我们想要”的开端都是对自己的爱,以至于人们甚至能够将爱与意志相提并论。我们爱我们想要的东西,我们想要我们爱的东西。
尽管恩典学说为意志自由设置了严格的界线,让意志自由变得根本不可能——但在奥古斯丁的意志作为自爱的理念中,闪现过一个非常现代的观念。相比于所有古希腊哲学,奥古斯丁从心理上将个体的斗争与分裂描述得更为透彻有力。在柏拉图的车夫看来,野马乃是不同的灵魂诸部分,这些部分是难以驯服的,因为它们寻求不同的道路。在奥古斯丁那里则相反,(灵魂)中间的分裂是由意志自身造成的。这位车夫不知道他应该驶向何方——这个冲突,冷静客观的希腊哲学并不了解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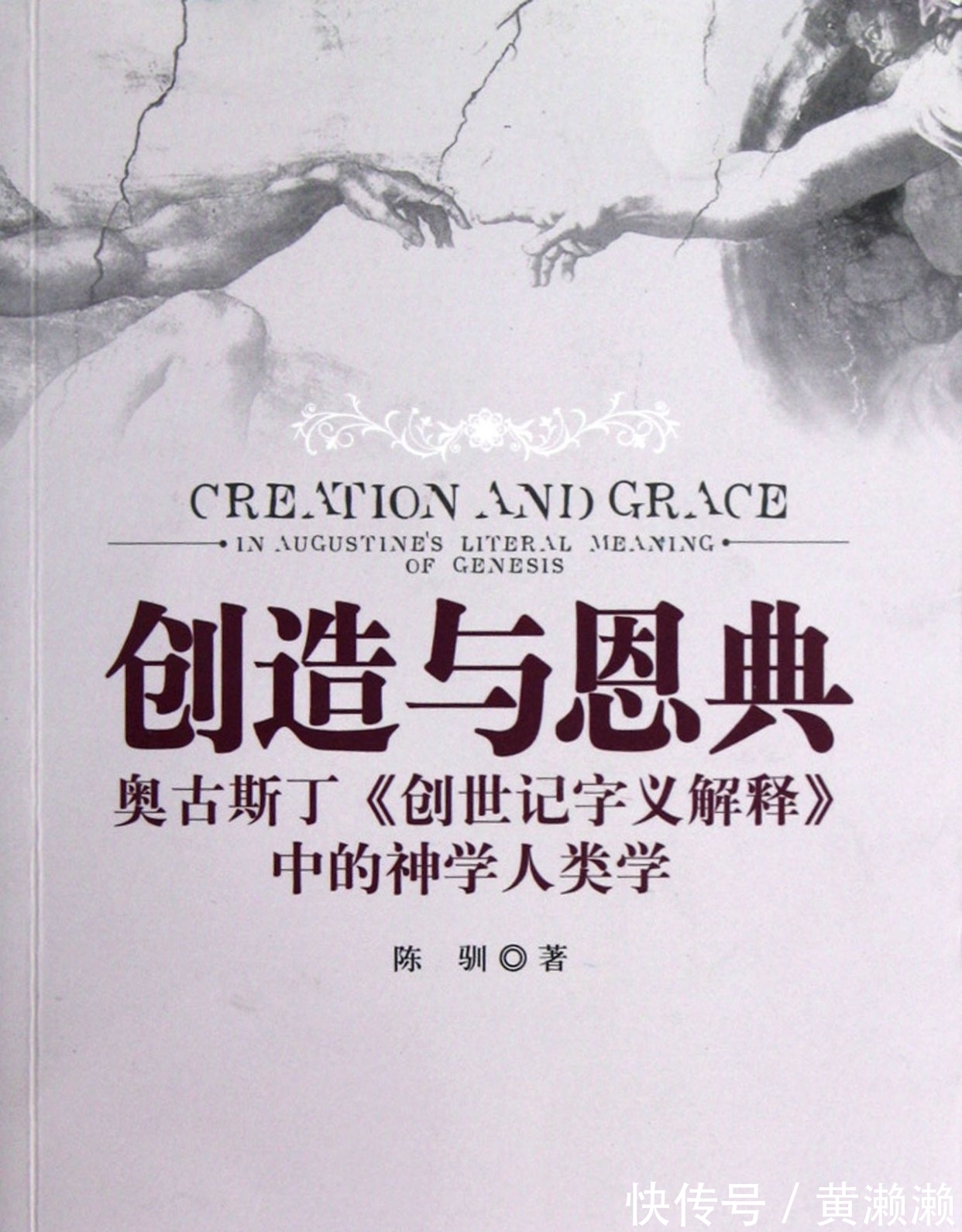
随着年岁的增长,认为对善与正确的认识是对过去所见之事的再回忆,这个观点在奥古斯丁眼中越来越值得怀疑。对他来说更重要的是,若没有上帝,更高级的知识、强大的意志决定就绝无可能。所以他在一些文章中以异常现代化的方式对语言做出了怀疑。人们到底能通过语词认识真理吗?在彻底的分析后,他得出结论:语词不是达到真理的特权通道,它顶多对“回忆”和“提醒”有用。因此,神圣启示的所有高级知识一直保留下来,却没有被领会。
关于理念如何从上帝的意识达到人类的意识这一问题,最后的答案恰恰是这样的:通过启发!只有得到上帝之光照亮之人才有可能接近真理。虽然在每个人身上都能找到这神圣启发的闪光,然而唯有被选中之人可以恰当地利用这神圣的知识之光。多数人却都没能做到。这种受到照亮的洞察保持为一种罕有的善,它将被选中之人与劣等之人分离开来。410年,不可思议的事发生了。奥古斯丁正处在权力与影响的顶峰,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国教已有30年,教会在神学和政治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稳固——然后罗马失陷了!
哥特人的统帅亚拉里克一世带着他的士兵攻陷了这座城市,将其洗劫一空。这不仅是对罗马帝国的沉重一击,也是对基督教教会的沉重一击!教会的思想家,比如凯撒利亚的尤西比乌斯连同他的《基督教会史》,以及他之后的哲罗姆教父,不都热衷于永恒的基督教的“永恒”之城?基督教好不容易终于实现了它在帝国的独家代言的要求,这座城市就陷落了——彻底离开了基督徒的至善的上帝。如果罗马诸神曾庇佑这座城市800余年,那么基督教上帝显然在第一个大挑战时就不灵验了。
上一篇:社科大与人民大学“牵手” 共同发力中国特色哲
下一篇:没有了